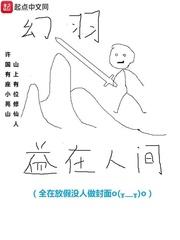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大道死而我不死,灵气枯竭我长青 > 第738章 南海见(第1页)
第738章 南海见(第1页)
李长笑躺在雪中。自入极域以来,他一直忙于奔波,不曾如何思考过。此刻望着黑夜,吹着寒风,不禁越想越多,越想越深。他又想到,扶摇天下的星辰,每年都要爆发几场大战。你打我,我又打你,打来打去,便是再八卦的人,听多这些消息,却也动厌弃了。扶摇天下充斥着大道之争、生死赌斗,道法手下见真章。那大道之争,说得大些,是道路相悖,容不得对方。说得小些,就是互看不顺眼,非弄死对方不可,否则记在心中,膈应得很。李长笑倏而一笑,修道之人心怀天地,但某些方面看,实则都是小气、偏执之人。但李长笑又想起,自己好似没资格笑别人。他自己也是这般。李长笑闭上眼睛,想起客栈时的旧事,与那一路上的种种见闻。忽然明白:“或许…她早就斗累了。”脑海中,浮现出媚三娘,倚靠在柜台前,一个人静静发呆的场景。当时不觉在意,只道这媚三娘行事作风难以常理而度之,最爱乱发脾气,有时多瞧她两眼,她就咯咯笑着,扭动腰肢,搔首弄姿,给你瞧个过瘾。有时又大骂登徒子,二话不说便是上手。如今回想,发现那老板娘,当时怕并非参悟什么至理大道,而是真的单纯,在苦愁自己家的客栈,怎么就是没人光顾呢?其时第一次去来去客栈。关白、二当家…都还在时,媚三娘还在惦记着她起得臭名。时不时偷偷换了牌匾。只是关白应赌约之后,媚三娘虽时常提起客栈起名一事,但已经没有真的打算换名了。李长笑梦观万事,凡人仙人都接触不少。他一直在走,一直在走,见过赵青那般,坚定的求道者,也见过王绝那般的赴死者。但无论是何人,走得久了,总会觉得累的。媚三娘与穆乘风,不知斗了多少载,恰逢灵气枯竭,难道她便不累吗。李长笑想起王绝寻到关白那日。媚三娘曾对关白说过,若不想去,便可不去。当时只道媚三娘安慰关白,如今看来,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说呢。可关白去了,因为他与穆乘风,有血海深仇,他必须要去。正因为关白去了,并且身死了,二当家也必须要去,他与穆乘风亦有血海深仇。如此反复,厨子也去了。等到媚三娘时,纵使满身疲倦,也必须要去应约。李长笑轻轻一叹道:“我竟现在才明白,你竟这般累了。”明白一路见闻,为何媚三娘的痕迹这般多。她不过是总停下来,休息休息,打打国王,当当女皇罢了。李长笑再有所悟,媚三娘一路多管闲事,只怕另有深意。媚三娘曾为关白觉得惋惜,一次酒后胡言,口中说着什么,人生来不该只为一件事情。如今看来。媚三娘自遇到穆乘风,便好似生来,便一直在不断证明自己,并非穆乘风的情梦道所化。灵气枯竭,鲛人族肆虐,媚三娘定然会在想,枉费自己机缘加身,占尽天下造化,历经不知多少载,才能结此道果。这等时世,却全用作私仇。想通这一点,更知媚三娘心中的疲倦,从何而来。故这一路上,她大事小事通通管尽,又常常欠下大债。也不知是料到了多年后,有人会沿路寻她,还是真觉得,自己是个欠债之人,已经债多不压身,再欠得多一点也无所谓。李长笑觉得是前者。因为他与几张卖身契,实实在在打了一顿架。当时打输了,便也像现在这般,大躺在地上。在李长笑心里,并不是真输,打不过那娘们。而是好男不和女斗,让她的。两人打架,媚三娘无所不用其极,各种阴狠招式,毫不留情的用出。李长笑却十分含蓄,怎么能是对手。但偏偏没折。正是想着,忽觉脸上有一抹温热。李长笑睁开双眼,见一缕阳光,破开云层,洒在李长笑脸上。竟似一温热素手,在轻抚脸颊。那诡异老人,见极夜过去,露出恐惧的神色,开始一步一步避退。李长笑定神眺望,见那漆黑天空,被一缕缕阳光射穿。天地间。风雪停了。李长笑沐浴在阳光下,全身上下,好生狼狈,靴子破了底,白衣破了洞。插在剑鞘上的梅花,也好似蔫了一般。他爬起身来,放眼望去,但觉天清地明,心头的云雾,也如极夜一般尽数散去。李长笑伸了个懒腰,鼓起气,高声道:“老板娘,我总寻不到你,我替你们去南海瞧瞧。”说罢,转身便走。然走不出几步,又忽想起什么事,快步走了回来。将剑鞘上的梅花摘下,放在鼻尖轻嗅,历经风霜,竟仍残留淡淡花香。他将花插在雪地上,又高声道:“我送一支花给你瞧瞧。”随后摆手离去。取出山海闲杂小记,边走边记道:“寻未果,但花已送到。”将小记合上,脚步却也停下。李长笑站在原地良久,开始左找找,右找找,忽的,翻出几片绿叶,那绿叶有宣纸大小,颇为奇特,其上的脉络,扭曲成一个个小字。正是媚三娘,在王七郎客栈签下的卖身契。李长笑高举卖身契,头也不回高声道:“还有一件事,忘记和你说了。你卖身契在我手上,我管你什么赌约不赌约,什么‘道’不‘道’,狗屁情情爱爱的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还不起就当牛做马,没得商量。”话音落下。天地间随即席卷起一股恐怖狂风,那疾风呼啸声中,竟隐约传来极致愤怒。竟想将李长笑手中的卖身契卷走,想将那持有卖身契的男人,剿碎为齑粉。李长笑通体霞光万道,自主护体免受侵袭,他慢悠悠,将卖身契收得完好,一步一步远去,身影逐渐变得虚幻,目光渐渐变得冰冷。在那急风中,一道似有若无的声音传来:“穆乘风,有胆南海见。”:()大道死而我不死,灵气枯竭我长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