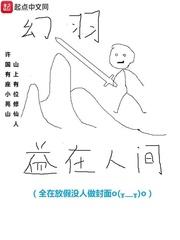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不辞长安花 > 命运的齿轮(第2页)
命运的齿轮(第2页)
*
日头毒辣的很,谢临出了殿门,立即就有个宦官弓着身子撑起伞。谢临余光瞥到了撑伞之人身上,发现此人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宦官。
“赵公公,有何事不妨直说。”谢临嘴上说着话,却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。
“丞相,陛下尚年幼,行事冲动,实在是无心之举,还望丞相莫要生气……”赵公公话未说完,谢临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。
“若是这样的话,公公就不必多费口舌了。臣还有要事在身,公公留步。”谢临挥挥手,自有谢氏的人撑着伞摇着扇子,护送其离去。
赵公公见那人远去,直到看不见他时,狠狠地对着谢临的方向唾了一口。
他们阉党不像这些权臣,无根无后的人,只能依附于皇帝。本以为户部尚书裴氏一案能狠狠咬上谢家一口,警告他们不要把手伸进内廷。裴氏血书死谏,卢氏大小姐击鼓鸣冤,本以为这件事是板上钉钉,谢氏就算权势滔天,也得顾及舆论。
谁知半路窜出个谢临,把那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他亲哥的头上,还迁带着卢家二房的一众人等,接连入了狱。此人当真是阴险狡诈,狠心至极。那是他亲哥,还是断了条腿的亲哥,硬生生的关进掖庭里折磨了一旬有余,出来时人已经状似疯癫,皇帝也不好多做苛责。
余下的卢家二房人,死的死,疯的疯,自尽的自尽。这线索就断在这里,舆论也平了。倒叫他谢临拣了天大的便宜,一举摧毁了卢家的势力。既扳倒了亲哥,又吞食了卢家。谢氏如今如日中天,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陛下只得感念他“大义灭亲”,赐他封侯拜相。
呸,拿鼻孔看人。
谁不知道他谢氏起家,是靠爬天后的龙床。如今倒翘起尾巴,装什么高风亮节。
赵公公吃了好一通闭门羹,他气急败坏地朝宫里走。如今也只有陛下待他宽厚,只是小皇帝势弱,阉党的实力是大不如前了。
*
谢临的马车浩浩荡荡驶入街坊,然而他却没往府邸的方向去,那辆奢华的马车浩浩荡荡驶向京郊。
“家主,大公子刚才喂了药,此刻还算安宁。”芜霜跟在谢临身后,向内屋走去。
谢临微微颔首,他一抬眸向前看去。
数十条又粗又长的铁链盘锁着一人,那人的皮肉早已被磨的溃烂,血水混着脓水,在潮湿的地下室里,被囚者只能听到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。
骤然听到声音,铁链中间的人动了动,看到眼前两人时,猛地挣扎起来,那铁链抖的声音震耳。
“照公子看来还认识一些人。”芜霜说,“目前的实验还不算稳定,他的记忆还保留了一些。”
谢临没有往前走,他示意芜霜退下,留下兄弟二人独处。
谢临自顾自地斟了壶酒,但他却没有喝,只是借着酒香,去除鼻息的腥臭味。
他缓缓开口,清冷的声音在幽暗的地下室里,显得更加空灵。
“大哥,咱们兄弟俩,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聊天了。”
“呃呃——咯咯——哧——”谢照的喉咙被涌上来的血沫堵住,他只能发出破碎的单音。
谢临自顾自地说,“你以为芜霜背叛了我,是你的人。但是芜霜,从始至终都是我的人。”
“我必须谢谢你,如若不是你,我不会如此快速得到她的血。”
“啧,宋怀谦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货,我可不想被他纠缠上。只能麻烦你,帮忙做这个恶人。”
谢照把链子抖的更厉害,谢临却轻蔑地笑,“大哥,被所有人背叛的感觉,不好受吧?”
“从一出生,就被利用、背叛、抛弃。可谁让你占了不该占的位置,生了不该有的心思。谢家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,又怎会轻易被你这样的外人拿去呢?”
“愤怒吧,你应该愤怒的。”谢临不痛不痒地激起谢照的怒火。
只有愤怒,才能烧光他的理智,让常山落雪与原血,更快速的融合。
父亲,你一辈子要做的容器,快要实现了。
谢临冷漠地看着眼前挣扎的人,恍惚间,看见了父亲的身影和自己重合在一起。
谢临将烈酒泼洒在地,像是在为他这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弟,祭奠第一杯酒。
酒液泼洒在地,蜿蜒曲折地爬向谢照上脚趾。
铁链上拴住的是毫无理智的疯子,铁链下站着的是极致理性的疯子。
命运的齿轮早在很久之前就已转动,只是巨轮下的人尚未被碾压,所以对它的恐怖,毫不知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