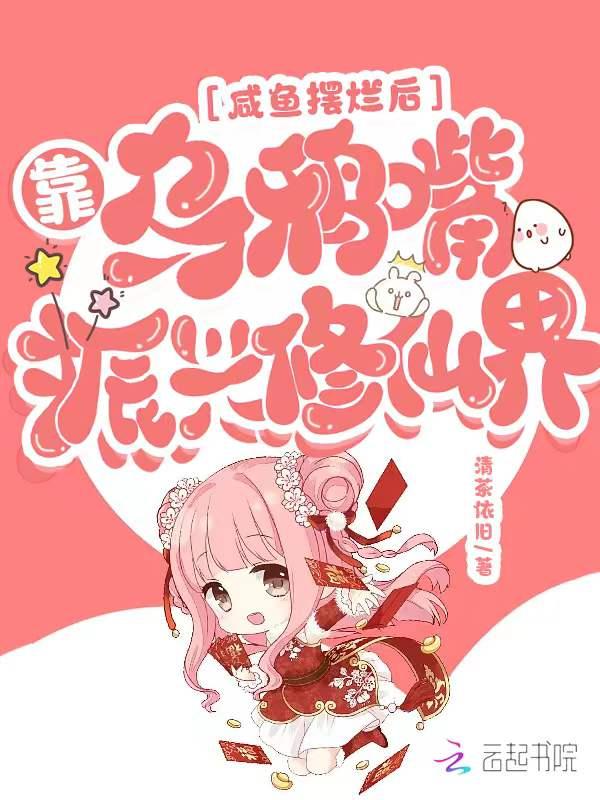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士何耽兮 > 第27章(第1页)
第27章(第1页)
夜澜忙带上祁铭墨:“花房栽了许多新种,孤认识的也不多,铭墨也来瞧瞧。”说实话,夜澜对男女之情所使甚浅,也不知道相亲培养感情是怎样的套路,若是问景离思,这个混账的回答大概是……把两人关在一个屋子里处一晚上,剩下的什么都解决了。夜澜当然不可能这么胡来,但也大致理解让两人相处的重要性,心下细细谋划着。陪苏濛认了“醉杨妃”,“二乔”,和“三学士“。夜澜故意讲错个把,祁铭墨陪着指正了几处,她好借坡下驴:”我在这方面的学问着实比不上祁公子,小濛若是有不懂的,问他便是,喜欢哪些种类记下名字,我差人给你挑好的送去,嗯……我还要去别处看一看,铭墨多照顾她。“说罢,给他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,便功成身退,将空间留给这两人。夜澜任务重大,义学一事的相关官员,夜澜过滤处帖子上的人名,一一过去打招呼,或是寒暄或是力赞,又依次按照品阶大小聊上几句……当皇帝,可真不容易啊。尤其和几位武官聊天时,还被灌了几杯酒,好在留了心眼将宴饮全部换成梨花白,味甘清甜,当水喝也好。在这一众浮嚣之中,总有一个另类,还是镇安王厉骁,夜澜思虑着,厉骁虽有个镇安王的尊位,权也极重,但与这宗族百年世家相比,根基还是浅了,可能是融不了这个圈子,于是想着便给他暖个场。实际上夜澜真的想多了,依照皇帝对他的器重和他自身的本事,想来攀交的人有如过江之鲫,且他披甲执刀,策马行街的猎猎英姿不晓得俘获了多少闺中佳丽的少女心,只是他本人肃气过重,叫人不敢前来交谈,少有几人厚着脸皮往上贴,都被他三言两语敷衍了过去,他一人坐在一处石案前,听着夜澜的步伐渐行渐近。嗯……大鱼上钩了。夜澜指了指他身边的一盆通体雪白的菊花:“这个叫鹤翎,你看它瓣形纤细密簇,是不是很像白鹤的翎羽。“又带他认了”松针“,再教他分辨”青心白“与”月下白“的不同,其实一直是夜澜在找话讲,厉骁看着她说话,默了一会,指着夜澜身上的绣纹:”陛下很喜欢忍冬吗?““……嗯,幼时母亲很喜欢,觉得这花能挨过冽冬,很是不容易,,而那时我只觉得这花很香,还能泡水喝,好看又好用,所以喜欢,后来才觉得这花真是不简单,蔓生的花,那么纤弱又那么坚韧。““很像陛下,又不像陛下。““啊?”厉骁看着她容色如画,水墨长衫更显得她身姿绰约,鸦发如漆散下,随风轻扬,更是撩在他心间,他突然像拽几句文化人夸人的话,好叫夜澜开心,憋了许久,郑重地对她讲:“远不及你坚韧,比不上你绝色。”“……你闭嘴。”夜澜磨了磨牙。☆、赏秋宴散宴之际,祁铭墨都没有等到夜澜,自己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京都贵女尴尬地聚在一处,两人都僵着不说话,苏濛一直在自己玩自己的,祁铭墨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夜澜是身影,酸不溜秋地盯着夜澜和厉骁言谈甚欢。心下又斟酌起夜澜离开的时候,递与他自行体会的眼神,妙目含光,盈盈生姿……莫不是就是自己想的那个意思?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当夜,祁铭墨按住夜澜的肩膀,轻舐着圆润的耳垂,另一只手在她纤细腰肢上细细摩挲,舌尖上移至她欣长的脖颈,埋首于精巧的锁骨处深吸一口气,那夜的陛下格外温存娇弱,依偎在他怀中,想是一朵颤着露珠的牡丹花,自他心间绽放,祁铭墨轻语低喃:“夜澜……”然后,就醒了。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薄汗,祁铭墨立刻躺好,试着能不能再睡回那个梦里,没成功。叹一口气,索性换了衣服起早一点。当真是魔怔了,才看了一会儿文书,父亲便唤他议事,书童引他到了父亲书斋前,他知道该有极重要的事情要议。书斋内茶香袅袅,祁老太傅于他抬了抬手,祁铭墨得了允诺,坐在他面前的软榻上,唤声父亲。祁太傅问了他赏秋宫宴的事情,他仍然心心念念着那个绮丽难言的梦,含糊应了句都好,然老太傅看他面色泛红,魂不守舍,怕是动情了,捻了捻胡须,看来陛下帮忙做的媒极为成功。嗯,陛下做事真地道。然后隐晦地谈起了与定国公的婚事,祁铭墨没费心思去听他说什么,正专心致志想梦境时,听到一句:“那就求一个好日子把事情定下吧。”“什么日子?”他问道。“定婚的日子。”“什么定婚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