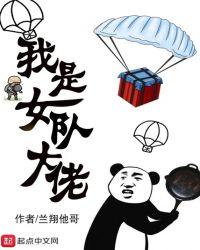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“琉璃” > 第135章(第1页)
第135章(第1页)
她声气儿幽幽地,到底还是年轻姑娘,一副心神不寧的样子。他有些揪心,居然体会到了一点苦难夫妻的味道。但也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,仔细盯了她两眼,&ldo;你不会是在我跟前唱大戏,糊弄我吧?
然后她生气了,板着脸说:&ldo;赶紧走吧。御前下了令儿,余大人遵旨办事去吧。
可他坐着没动,语气倒是放轻柔了些,&ldo;挺过这段时间就好。不过我有句话要交代你,上头越是留意你,你越要给我老实些,別露出一点马脚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又在打歪主意,到时候大不了先宰了你,再负荆请罪。上头那样的明白人,不会为个死人和我过不去,你明白我的意思吧?
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恫嚇,这招对如约来说已经没有太多威慑力了。她知道他捨不得动她,现在说得越狠,日后维护起来越卖力。她也不是没想过,趁着他对她放松了警惕,干脆在他饭食里下个毒,毒死他一了百了。可她的身世並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,他的那些办事弟兄,一旦发现他有了闪失,必定头一个来揪她。她是既要让他死,又要保得自己全身而退,想留下这条命,再去和罪魁祸首拼一拼。
所以她苦笑了下,&ldo;我这是两头受催逼啊。本以为同大人诉诉苦,你能明白我的心思,没想到雪上加霜了。
这话说得他无言以对,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些过分了。万一她是真心向她求助,自己这样岂不是寒了她的心吗。
他不会认错,但態度还是转变了许多,忖了忖道:&ldo;就让涂嬤嬤时时陪在身边吧,零碎活计让那两个丫头去办。
边说边又上火,朝外望了眼道,&ldo;派她们来伺候的,她们倒好,受用去了,连个人影都看不见!
如约怕他迁怒底下人,只说是自己让她们歇着去的。他待不了太久,到底站起身预备离开了,她送他到门前,淡淡叮嘱了一声:&ldo;才下过雨,赶夜路要小心些,路上湿滑。
本来很家常的一句话,但在余崖岸听来,却像天上的仙乐一样顺耳。
他站定了脚道:&ldo;御前还有另一道令,承办完了先帝落葬事宜,我又得赶着去陕西。
这下她呆住了,&ldo;怎么还要走?要去多久?
他说:&ldo;说不准,少则两个月,查办庆王,预备削藩。
她脸上的失望掩也掩不住,&ldo;要去那么久
能赶上回来过年吧?
她皱着眉,细细地抱怨,真像个捨不得丈夫出远门的小媳妇。他心里一热,就什么都顾不上了,伸手一拽,把她搂进了怀里。
他躬着身子,只为尽力抱紧她,喃喃在她耳边说:&ldo;我也不放心把你放在京里,这一走,好些事就不由我掌控了。我怕皇上不死心,更怕你翻浪花儿。
话还是照例那么不中听,他胸前粗麻的孝服磨着她的脸,有种刺而痒的感觉。
她厌恶他的怀抱,但她必须说服自己接受。心里作了许多准备,慢慢抬起僵直的双手,抓住了他孝服的后背,嘴里怨懟着:&ldo;你要不会说话,那就別说了。
他察觉到了她的回应,这一刻几乎高兴得要蹦起来。看吧,这小丫头果然是能调理过来的。相较於陌生男人的虎视眈眈,至少自己和她一个臥房里睡过几晚。此番戒情断欲不是无用功,给了她一点时间,她两下里权衡,到底还是转过弯来了。
她害怕皇帝的那双眼睛,倒也好,至少短期內老实了,应当出不了什么岔子。
&ldo;回京之后在家陪着母亲,哪儿也別去,宫里碍於情面,总不能让人特意来传你。
他又留恋了片刻,最后还是松开她,倒驴不倒架子地又追加了一句,&ldo;別打什么不该有的小算盘,一切等我交了差事再说。
如约听话地点点头,又垂眼看他手里那串菩提,&ldo;这个怎么处置?
余崖岸咬着牙,什么都没说,把它塞进了袖袋里。
再不能耽搁了,他打开门,带上近身的随从,大步流星朝甬道那头去了。如约站在门前目送他,看他半道上遇见莲蓉,十分没好气地喝了句:&ldo;机灵点儿!
莲蓉嚇得缩脖子,盆里的水都险些泼出来。这样横行霸道惯了的人,不难怀疑连路过的狗,都会无端被他踹上一脚。
好在人很快走远了,莲蓉这才闷着头把水送进房里,战战兢兢道:&ldo;大人不知怎么发了脾气,別不是和夫人闹不痛快了吧!
如约说没有,&ldo;公务上碰了钉子而已,不碍事的。
等莲蓉把盆儿放在架子上,她走过去仔细盥手,一面吩咐她:&ldo;明儿起,你和涂嬤嬤轮着在我身边伺候,跑腿的事儿就让翠子干吧,我跟前別离了人。
莲蓉不大明白,先头不愿意让人陪着,怎么这会儿又让別离人了。
如约见她嘴上应承,脸上还有些不解,便同她解释:&ldo;大人先行一步,上敬陵办差去了。其他命妇的丈夫都随扈呢,只有我孤身一个。你们在跟前,进出都有个伴儿,就不怕生出什么閒言来了。
莲蓉连连答应,&ldo;怪道呢,奴婢看大人急赤白脸的,刚才那一嗓子,险些嚇我一个倒栽葱。
如约笑了笑,接过手巾仔细擦了手。就寢的时候让莲蓉把涂嬤嬤叫来,说夜里孤零零地,害怕。
()
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