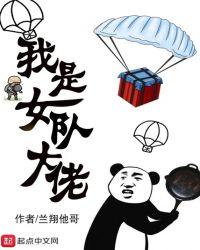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末世的修仙者 > 华似(第2页)
华似(第2页)
眼前男孩褐短上衣,一手持枝,另一手护在胸前,架势和先前只顾抵挡后退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但那凌厉的气势转瞬即逝,突发奇招制住女孩后,收回树枝又成了原先略显笨拙的模样。
原本在一旁观战的人瞳孔微张,想不到这小子不声不响的,竟能使出这招。收势后,那孩子目光随即滑向身后,见那人没什么表示,庆幸之余有些失落。
两个孩子又对了几招,终是女孩占了上风。
“你赢了。”男孩弃了枝条,坦然认输道,“我现在功夫不及你。”
那女孩也抛开树枝,欢欣道:“我是赢了,不过你也不差,刚才真是吓了我一跳。那招好生厉害,你是在哪里学的?”
“不能告诉你。”
“哼。小气。”女孩眼珠一转,改口道:“反正还是我赢了。怎么样,要不要认我当老大呀?”
男孩坚定摇头,随后果断挪回青袍那人身边。那人看他们稚气未脱,轻笑一声,也不多话,只由他们打闹。
几人行过一阵,不觉天已擦黑。月升日落,暮色四合,道旁树影泼墨般覆遮下来,容屿城巍峨的剪影逐渐显露在小道尽头。
原本以为今夜要在野外度过,遥遥望见城墙角楼,两个孩子都不免心中雀跃,加快了赶路的步伐。到了城墙脚下,堪赶上闭门前最后一次排查。经过守卫一番例行盘问,三人终于进了城。
城内外是完全不同的光景。
城外一片沉静,过了月城,城内却人稠物穰,层台累榭。鳞次栉比的街亭楼阁中,华灯初上,行人过客络绎不绝,纷繁往来穿行其间。虽是夜晚,在各色彩灯的环绕下,比白日还要辉煌明亮几分。
青袍那人行在前头,一帘轻纱遮盖面容,跟着两个玉琢似的小孩。如此怪异的组合,路上引得不少人回头观望。
男孩看看这个,摸摸那个,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有趣。而那女孩倒是一副轻车熟路的模样,时不时还给介绍些风土事物。
不消多时,几人拐进一条巷子,来到一个酒肆前。酒肆门庭略显简陋,酒幌上悬着一个大大的“天”字,槛内却几乎不见有客,偌大个酒馆门可罗雀。
青袍那人走进店里,径直越过形形色色的酒瓮酒坛。店里也是空空的,只有一个掌柜的窝在柜台后面,面前路过几人,却连眼皮也不抬一下。
“这要有生意才怪啊。”女孩紧紧跟着那人的脚步,嘴上还不忘感慨。
两个孩子随着那人一起走至偏屋角落,只见她抬手扶住案几上盛酒的瓷瓶,另一手绕至瓶后,扯住什么,用力往外一拉。
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悬满杂物的旁侧墙上,倏尔现出一道细缝。那人信手一推,墙后竟现出暗道来,两侧燃着烛火,幽幽不知通向何方。
晃神的功夫,那人已闪身进了暗道,男孩紧随其后。那女娃向四周又张望了一番,才急急跟上。片刻之后,身后的墙面弥合如初,三人的身影在墙后完全消失不见了。
几人在昏暗的通道中穿行约莫半炷香的时间,前方豁然开朗,到了一处屋舍俨然的所在。那女孩瞠目结舌,尽管她在这城里长大,对城中事物十分熟悉,却从不知道在闹市之中竟还有如此隐蔽幽静的庭院。
庭中三三两两站着几个形貌各异的人士,正谈论些什么,见三人进来,只淡淡看了一眼便不再关心。楼阁间不断有身着灰袍的童子抱着文书穿行,脚步匆匆,繁忙之下却是一派井然有序。
顺楼旁盘旋的木梯拾级而上,大堂四面通透,正当中摆了一方半屋大的环形台桌。桌后端坐着灰袍高髻的三位文士,正将手边堆叠如山的木牌分门别类,栓挂到身后密密麻麻的银丝上。信手一扯,悬垂的木牌便随银丝一道迅速消失在屋顶。
两个孩子看得目不暇接,伏在栏杆边竟忘了走动。直到青袍那人伸手扯了扯,他俩才晃过神来,跟着一起再往上行。
直爬到三楼,又拐过一个拐角,几人才停在一扇闭合的门前。
“你们在这里等一会,不要乱跑。”那人说完,自己推门进去,合上门便没了声息。
留下两个小孩站在门口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等待的时间总是十分漫长,两人面面相觑蹲了一阵,又伏在栏上向庭中望了半晌,迟迟等不着人出来。
正当那女孩儿嘀咕着要去别处探探时,拐角那头忽然传来颇为急促的脚步声。两人转头看去,见墙边先是扬起一角白袍,随即风风火火转出一位面如冠玉的年轻公子来。
来人大步流星,及靠近门扉,才抽空往趴在栏前的两个孩子那边瞥了一眼。
“是你?”“怎么是你!”
那人和女孩打上照面,异口同声惊叹道。
“秩午哥哥?你怎么也在这里!”那女孩显然极为震惊,她看看来人,又看看面前紧闭的门扉,“你早知道这个地方了吗?”
身着白袍的男子揉了揉额角,叹气道:“我还想问你呢,你为何出现在此处?”
“我可是有人带,正经走路进来的,才不是翻墙钻洞!”女孩颇有气势地回驳道。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“那你倒说说,你为什么也在这?”
男子像是有什么急事,撂下一句“稍后再找你解释”便要进屋。正回身要推门,紧闭的门扉突然被里面的人打开。他去势未收,险些朝屋里栽倒,站定后长吁一口气,这才抬头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