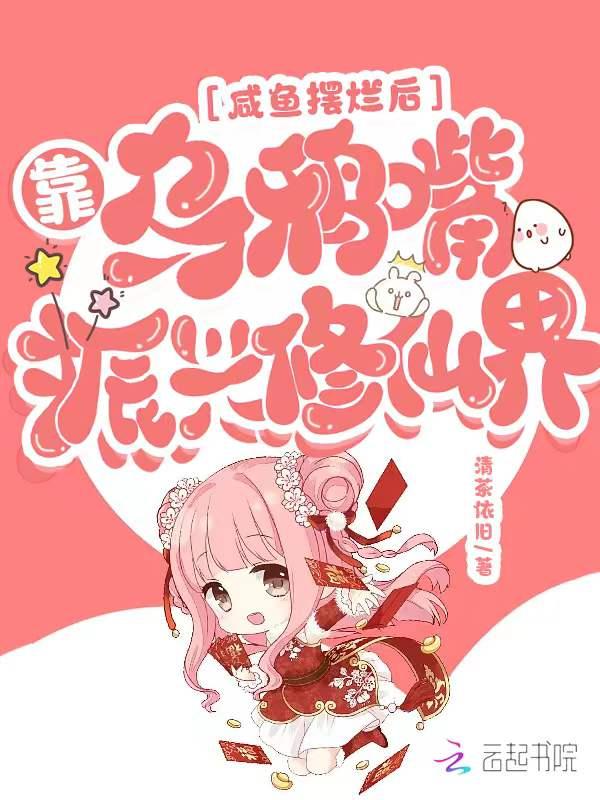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清明扫墓开局祖坟炸了 > 第257章 爱是常觉亏欠(第1页)
第257章 爱是常觉亏欠(第1页)
美人簌簌落泪,看得谢庭江心如刀割。婉宁有许多事不便与玉衡讲,他却是知晓的。便也时常觉得自己无能,亏欠了她们母女二人。低声啜泣好半晌,孟婉宁才止住了泪,心中是前所未有的松快。她温声道:“此次前来上京,也是想看看我家玉衡,过得好不好。”“且看这江陵侯府中,玉阶彤庭,画栋飞甍,园中花草亦是名贵品种。”“我便也把心揣回肚子里,知你往日寄回家中的信笺,并非报喜不报忧。”“那是!玉衡出手,定叫八方牛马蛇神,俯首称臣。”谢玉衡昂着头,脸上尽是少年的春风得意。孟婉宁好笑地点了点她的鼻尖,宠溺道:“你啊,就会逗为娘开心。”“还有一事要同你说,四月里不是准了益州、交州两地,同邻国通商之事。”“七月下旬,有从磐启国回来的益州商人,在江陵兜售蚌珠。”孟婉宁招来侍女锦绣,吩咐其去马车内取一物什。不一会儿,锦绣捧着精美的沉香木匣子回来,将其轻轻放在谢玉衡面前的石桌上。啪嗒一声,匣子打开。几颗与铜板一般大的蚌珠,躺在丝绸上,流光溢彩。谢玉衡捡起一颗握在手里,细细把玩。其个头圆润,质地细腻似玉,触如上品羊脂。“据大梁地理志中记载,自益州去磐启国,需翻越昆仑墟。”“便是今年去,明年也一定能回。这”谢玉衡看着手中蚌珠,颇为不解。孟婉宁净了面,拿帕子擦拭着下颚的水渍,笑道:“那益州商人说,他们是打益州南部永昌郡出发。”“到了掸国走水路出海,之后再转海行,便到了磐启湾。”“磐启盛产蚌珠,瓷器茶叶丝绸之类的,却是寥寥无几。”话说至此,谢玉衡便也知道了娘亲是什么意思。大梁出口乌孙以西的商路,被池家外甥把控。若能在磐启湾一带,开辟另一条水上丝绸之路。虽不及乌孙之路,途经国家之多,亦能以物换物,赚个盆满钵满。将无关的下人都屏退了去,谢玉衡望向孟婉宁,其眸如明珠,神采奕奕。爱人如养花,娘亲已经变成食人花啦!“不过玉衡听闻天竺人也擅织丝绸,磐启人何不买邻国的?”“反舍近求远,购买大梁的丝绸?”谢庭江哈哈一笑,与有荣焉道:“自是天竺人的丝绸,织样粗简了些。”“不像你娘亲绣阁出品,巧夺天工,栩栩如生。”“不然那益州商人,何苦千里迢迢跑到江陵来。不如立马折返,还能赶在年关前大赚一笔。”孟婉宁嗔他一眼,拉起谢玉衡的小手,心疼抚过其指间的薄茧。“海上多风险,且磐启国小,所能吃下的丝绸恐是不多。”“我打算九月里,亲自去扬州收丝绸。届时行踪飘忽不定,恐你忧心,便提前来与你一道说了。”九月谢氏书院秋学已开,谢庭江自是不能陪同一起去的。谢玉衡略作思量,便让容时去取楚珩赠她的白玉来。反正在京刷脸就成,也用不上这玩意儿。“既然磐启国那边,对精致的丝绸制品感兴趣,想来掸国和万象国亦是如此。”“万象国一年四季多炎热,想来扇类需求多一些。”“娘亲也可同交州商人接触接触,不过啊,需得拉上一些同盟,一家独大,易成靶子。”“知道啦,就属我家玉衡脑瓜子转得快”说话间,司远道也从衙署回来了。匈奴人活跃于秋冬之季,兵部亦忙于此时,不时休沐也加值。寒暄几句,司远道便抓着谢庭江,到书房开小灶补课去了。教不了儿子,老子勉强还能再教教。临近晌午,许律耷拉着头,如行尸走肉一般,穿廊而来。“哟,一会儿不见,许大公子这是咋啦?”谢竹书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,叫这厮先前拿糖葫芦黏他头发。哈哈哈哈,遭天谴了吧!许律都懒得理他,直接略过,一屁股坐到谢玉衡旁的石凳上。自袖中掏出一纸,拍在桌上。谢玉衡瞥见纸上太平坊地契几个字,就想笑。促狭的目光,在许律身上打了个转。谢玉衡揶揄道:“这太平坊的房子可不便宜,许家主真是舍得下血本。”许律:“”谢邀,他今日在梨园戏班子挂了个角,出演尸体。许律重叹一声,脚勾住石凳柱子,顺势一躺霸占了好几个石凳。少年的袍角落在地上,目光看向天上。未明自己心意时,便觉得无一人可与那人相配。明晓自己心意后,亦是如此。爱常使人自卑,常觉对方如天上之云,不可高攀。恐她选了别人,又恐表明心意后,连现下的朋友关系都无法维系,此生陌路如过客。一张脸突然出现在许律的视野内,谢春喜伸手拍了拍他的肩。“可是庶常馆课业太重?或有不明之处?”谢春喜语气犹如邻家长辈一般和蔼,轻柔。许律身子一僵,立马坐起身来,“没,没有”谢竹书不知从哪端来一碟葵花籽,坐在谢玉衡另一边。两人边嗑瓜子,边看此二人唠嗑。咔吧咔吧的嗑瓜子声,不绝于耳,听得谢春喜莫名其妙。这瓜子,有这么好吃吗?谢春喜伸出手抓了一小把,磕了几个,感觉也一般啊待谢知意从城南义诊回来,见到的便是几人凑一起,嗑瓜子的诡异画面厉害了我的爹,吃自家的瓜!好在没过一会儿,就有下人来邀,“饭菜已摆好,诸位请移步饭厅。”热闹的午饭过后,又小歇了片刻。直到下人来报,开市鼓已经敲响,谢玉衡几人这才出发去东市。东市最大酒楼,今日却不对外开放。谢玉衡等人从后门而入,由户部官员领着,一路上了三楼临时搭建的包厢。往下看去,一楼大厅已是人满为患,热闹如菜市场。许律从纱窗边折返,走到桌旁。抬手给自己倒了盏茶,一盏接一盏。:()开局祖坟冒青烟,女扮男装科举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