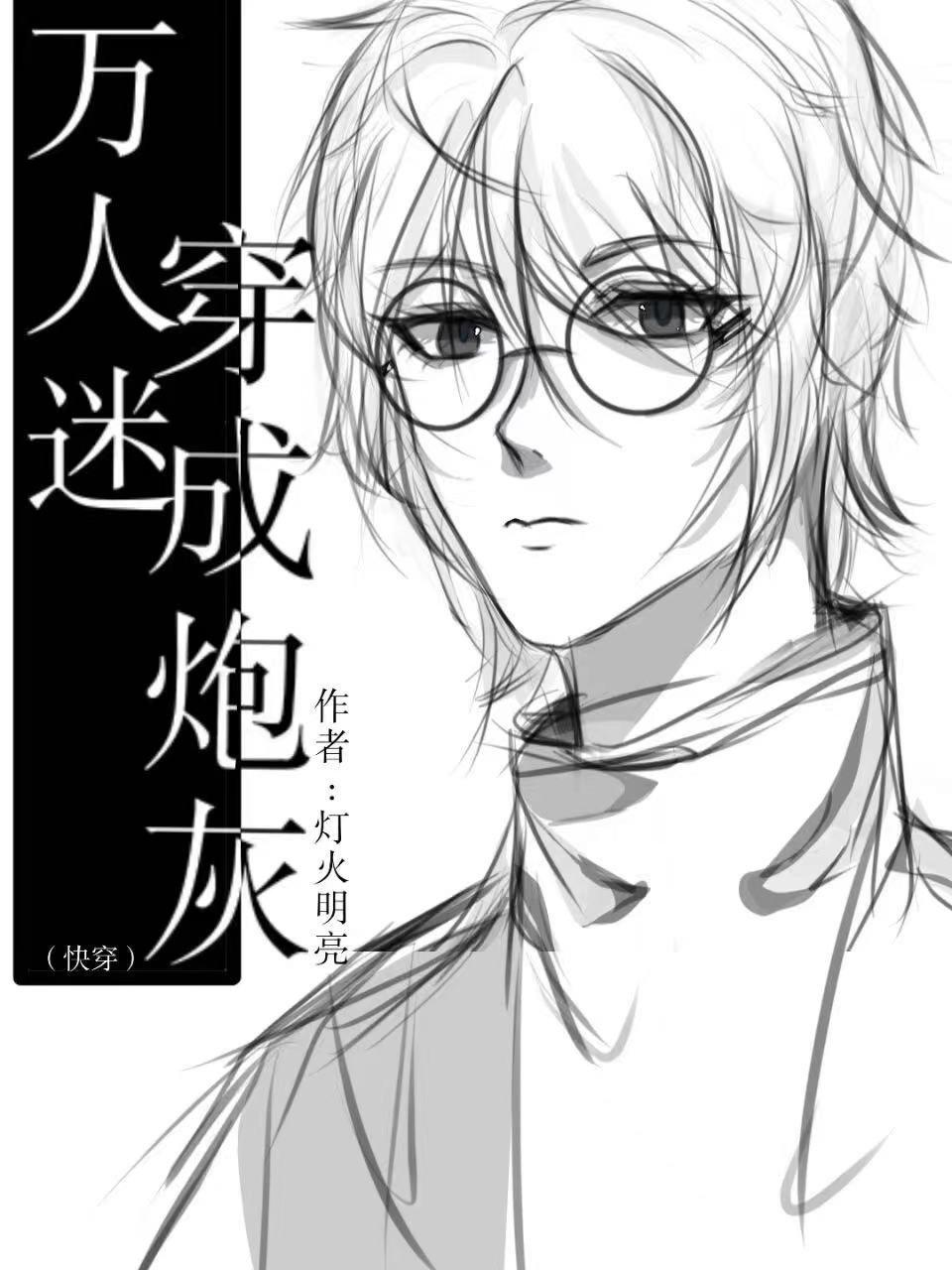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孤与太侍君免费 > 第11章(第3页)
第11章(第3页)
“殊听到了,送梨汤的郑嫔的声音。”
“送琼浆玉液都不去。”
本就是想和虞殊两人来逛的,再加几位,那还叫什么私会。
“好,”他伸手搀住了我,托的位置不是裘衣袖口,而是手腕,道,“天寒路滑,殊扶着圣上。”
我的胳膊只要轻轻一滑,就能与他十指相扣。
很难说他不是故意的。
我算是看出来了,他又想得多又爱醋,还喜欢故作大方,说一些绕圈子的话叫我踩陷阱。
真是的,孤看起来有那么不解风情吗?
好像是有点。
我回顾了一下,然后哽住了。
母妃曾说过,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,人会想方设法,不停地去寻求某个问题的答案。
因为不放心,没有回头的机会,就怕一步踏空,走错了路。
虞殊这般作态,是我没有给够他安全感吗?
可是,我怎么做,他才会少想一点,踏实一点呢?
我不知道。
我决定再去问问太傅。
不过,目前情况下,虞殊都已经表示得这么明显了,我当然不能假装没看见,叫他心头落寞。
于是,我紧紧地扣住了他的手,把那微凉的指节往暖融融的长毛袖口中拉了拉。
“走。”
脚不方便就是不好,牵着人走的背影一瘸一拐的,一点也没有美感。
不知道虞殊瞧着,会不会觉得好笑。
我叹着气一回头,发现他居然真的在笑。
“你不许笑!”我无赖道。
虞殊“嗯?”了一声,问,“为何?”
“孤要面子,”我一边说,一边不好意思地把音调拉低,“若不是伤到了,孤走起来还是很英姿飒爽的。”
“圣上误会了,殊笑的不是这个,”他为我拨去了被寒风吹到眼角的碎发,“殊只是高兴。”
“哦。”
他离我一近,我就要脸红。
为了不在他面前露怯,我悄悄退开一步,复又匆匆忙忙地要拉他向前。
其实我们已经在梅树底下了,但我有种莫名其妙的,需要忙碌起来的感觉,总想找点什么事情干一下,好表现得不那么紧张。
虞殊在原地没动,道,“圣上,您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,再走,脚踝会肿的。”
“孤没觉着疼,”我说,“不会有事的。”
“等疼了就来不及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