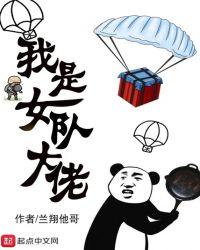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夏风长 秋雨短 红叶如绸 醉后枫林晚 > 第 68 章 回甘(第1页)
第 68 章 回甘(第1页)
南城的气候似乎没有春天和秋天,它们停留得短暂。
悬铃木重新长出舒展的新叶,气温就已经能穿上薄衫。
在下学期开始后,夏思树在课业之外找了一份兼职。
工作是江诗介绍的,时间的灵活性或是薪资都很好,同期的兼职生还有另外两个,同样的待遇,直到她差不多在那兼职了两个月,才见着了那家公司的老板——江支闵。
两人只打过几次照面,与其他的老板和员工一样,江支闵没因为对她有过追求性的行为,而给她额外待遇,又或是其他越界的举动,于是夏思树照旧还是在那待着。
那几个月她的大部分时间,只在学校、出租房和公司三点一线的距离内来回,脱离了邹风的生活圈,身边也不会有人无意识地再向她提起。
而就在那个月,周逾在美国出了场车祸,右腿骨折,周家父母忙于生意,抽不开身。江诗请了两周的假,订了最近的一班机票,去了美国看他。
“是不是有点像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二傻子。”江诗晃着手机上的机票信息,无所谓地朝夏思树笑了下:“我还是喜欢他。”
那个年纪太难说是对是错,也来不及思考及时止损或是利害得失,有的也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勇气。
那天是周末,夏思树将她送到机场,登机前她抱了江诗一下,弯着唇,祝她一路顺风。
“你也别太想我。”江诗将鼻梁上的墨镜拉下来,笑着朝她招手告别。
送完江诗,从机场出来后,夏思树形单影只地站在出租车的接车处,头顶是机尾拉出的航迹云,空气中已经带了热浪。
她的神情大多时候还是漠然的,似有些心事,裙摆和勾着手臂的发梢被风轻扬,等车的间隙,她兜里的电话响了两声,夏思树低下眼拿出来看,是夏京曳的电话。
差不多从夏京曳到了新加坡后,夏思树经常收到银行卡内转入金额的提示信息。
转账的时间不怎么固定,但频率大于一月一次,金额偶尔多偶尔少,像是签了单子又或是因为其他事,想起了她夏京曳就会给她转过去一笔钱。
这次的电话,夏京曳说到最近购置了一套新房,只有她和一个保姆常住,问她马上暑假,要不要到新加坡待一段时间。
通话沉默了几秒。
“嗯。”夏思树点头,没拒绝,坐在出租车上,朝着外面微刺眼的阳光眯了下眼,说道:“不过要七月末才有时间。”
夏京曳在那头“嗯”了声,似乎还在工作,背景声有些嘈杂,她开口道:“那你要过来之前告诉妈妈一声。”
“好。”夏思树回她:“知道了。”
说完,她挂断电话。
一通电话简单结束,兼顾着学业和工作的大学生活是忙碌的,同时夏思树还在准备着转系。
在大一学业结束后的那个盛夏天,去新加坡的七月底前,夏思树终于有时间去了趟西港,去邹风临走前说过的,那个她自己的家。
飞机落地的时候那天是下午,走出机场,这座城市依旧和往年一样炎热而潮湿,道路干净,蒲葵树沿着海边的风乱舞。
夏思树照着包裹中的照片和地址,打了辆车过去,直到车开到了一处欧式独栋花园的别墅区下面。
那会是五六点的时间,红色的屋顶笼罩着金黄色的日光,这片别墅区有些年头了,坐落在半山腰,周围绿植浓密环绕,道路边稀稀拉拉停着几辆私家车或保姆车,十几年过去,这边依旧还有住户。
夏思树抬头看了眼被爬山虎藤蔓缠着的房顶,她沿着那道缓坡一直往上走,直到这片别墅区的最后。
她对这里是有些印象的,她记事早,爸爸那个时候常夸她聪明。
直到日光消逝之前,夏思树走到了那处门前,门牌号32号。
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,门前却不像想象中的荒芜,反而被打扫得很干净,连那两扇闭合的铁门都有重新翻新刷了一层新漆的痕迹。
西港的风吹着,夏思树肩头沾着点夕阳的光线,发丝随意地披散在身后,她穿着简单的宽松白t和牛仔裤,脖颈上悬挂着一根黑色绳子,就这样站在门前停顿了会,胸前跟随呼吸轻微起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