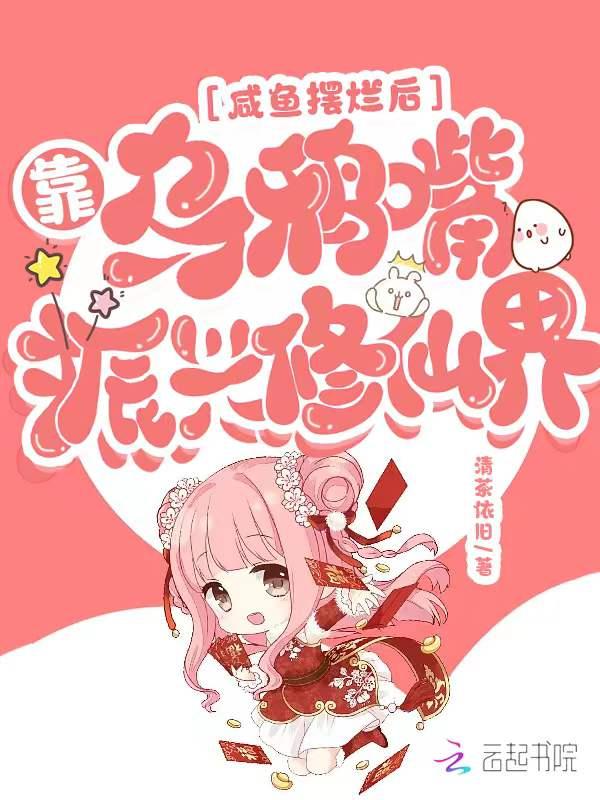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绍宋是什么意思 > 第八章 畏惧(第10页)
第八章 畏惧(第10页)
刘子羽为之一滞,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说他眼界低了,关键是那个说他眼界低的人如今也成了‘受制于眼界’之人。
“譬如说,你们这些人,主和的、主战的、主守的,无论对金立场如何,总是跟朕说什么制度章典,论什么成例家法,好像只要稳当下来,重建制度,便可以万事大吉了。”赵玖摩挲着手中棋子,幽幽言道。“可实际上,依朕来看,只说军事上的事情,这大宋朝的成例家法还有制度越是执行妥当,却越只能坏事!因为大宋军事上的成例家法制度,一开始便是防内而虚外的!用你们的法子,这大宋反而亡的更快!”
刘子羽听到‘防内虚外’四字,如遭雷击,当即便要开口,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,旁边小林学士也稍微回过神来,似乎也想要说什么。
不过,言至此处,赵官家已经如开了闸的什么一般,已经停不下来了。
他扔下棋子,从廊下站起身来,负手看向了明显有些失态的刘子羽,却是恳切相对:“彦修,张德远说的对,朕确实忐忑不安,但不安的缘故不是无所适从,而是恰恰太清楚该怎么做了!你说的也对,朕似乎对金人撤走之后的局面有所畏惧,但朕之所以如此,不是因为喜欢打仗杀人这种野蛮事,而是相较于这些事情,另外一些事情太难了!那些事,本朝只有一个王安石尽心尽力去做,还差点被人污蔑成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。实际上,若能苟且太平,凑活过个百年,朕又何尝愿意做这种事呢?可这不是时不我待,这不是负着多少人期待,负着靖康之耻,负着两河中原多少条人命,决心要做个好官家,决心要亲自施为,决心去改天换地吗?不做,怎么办?而要做,又怎么会不畏惧?”
刘子羽和小林学士都已经听傻了,便是旁边的冯益也都双目滴溜溜的转了起来。
“而这,其实便也是朕为什么明知道李相公还有其余几位,都是天下难得的真正想要抗金的同志,却把他远远摆在东南的缘故了。”赵官家继续叹道。“真让他主政固然无妨,或许一二十载后,终究还会有个大略兴复局面,但朕既然决心要认真施为,却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绕圈子、费功夫了……彦修,金人没那么强,朕也知道该怎么走,你不必忧虑!也让张德远不必忧虑!”
“臣惶恐,竟不知官家志气。”
“其实,这话也是憋了许久的,朕早想找人说一说,你既然替张德远来问,朕便顺势倾诉一下而已。”赵玖忽然再笑。“不必过于在意。”
刘彦修如何能不在意?
不过另一边,赵玖又何尝真的将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了呢?
大宋文官政治的整体保守;金人不力尽的话,就不会给大宋留下喘息之机;宋代军队的全面腐化;将来金人之后可能的危机;还有下定决心与岳鹏举争一争功的个人野心或者志气……怎么可能都对着一个才认识几日的刘子羽倾诉出来?
无外乎是这位赵官家从胡寅到张浚,陡然意识到了自己那可怜班底对他这段时间表现的担忧,所以借此人将话递给张浚,以安人心罢了。
“官家!”
就在这蔡州府后院再度安静下来以后,还没有一炷香功夫呢,正当赵官家细细点数棋子,发现不足,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,忽然间,刚刚接到旨意应该不久的御营统制呼延通便狼狈自外闯入。“官家!哨骑刚刚出发便匆匆回报,说是西面居然有贼人到了!”
“慌什么慌?”赵官家将地上好不容易寻到的两个棋子拈起,放入身后冯益捧着的钵盂中,方才随口呵斥。“有甚可慌的?朕都没慌!你说你身为城中唯一主将,怎么能露出畏惧惊慌之态呢?”
呼延通瞬间羞惭入地。
ps:这是卡了,不是我的锅吧?!还有,章节名标错了,不影响阅读,大家不要在意。,!
言道。“天祚帝与霞末如出一辙,皆是闻得银术可引轻兵奔袭而来,便孤身而走,而且是一个弃城、一个弃军而逃,结果都被银术可事先派出的绕后小股精锐轻松擒拿。至于太原之战,却是往援兵马被身后中枢逼迫,分多路向前,却又互不统属、且前后进度不一,所以被他与完颜娄室从容绕着太原城一一拔除……你听明白了吗?”
宇文虚中低头不语,显然是听明白了,但其他几位相公却也显然是没听明白。
“官家,还是速速发金牌召韩世忠、王德归城下妥当一些。”等官家一住嘴,吕好问便恳切相对。
“或许可往南面光州稍作躲避。”许景衡也紧张万分。
见此情形,赵官家实在是不耐,却是长长的呼了一口气,然后呼啦一下掀开了一侧棋盘,露出了藏在下面的甲链。
院中瞬间愕然无声,一时只有花树摇曳,光影交错,外加满地黑白棋子点缀于绿地之上,若不是有个敢杀人的天子在发脾气,还真有点春日盛景之态。
“非要朕将难听的话说出来吗?!”
赵官家带着一股气闷站起身来,却是拽着那片甲链在廊下负手而行,然后忽然回身,厉声相对。“你们以为你们真知兵吗?!你们若知兵,何至于太原败成那个样子?!何至于有靖康之耻?!朕早知道银术可或许将至,几乎就要着甲了,之所以强做无事,只是忽然想起来,城中还有你们这些大惊小怪之人!若是强行着甲,反而会让你们慌乱!今日的事情,朕跟你们说明白了!城防自有呼延通去处置,你们不要干涉!这些军务上的事情,你们如果能装聋作哑,便是天下之福!”
“臣惶恐,不堪为相,请辞……”
“请什么辞?”赵玖愈发大怒,却是将甲链掷到地上。“金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便来,此时受点委屈便要请辞……你们委屈,朕不委屈?每次作战,朕都要又哄着前面,又哄着后面,一会忧心前面的军士被军官截了粮饷,一会又要防着后面你们乱插手,一会要提醒前面军士不要以朕的安危为念,一会又要想着你们说什么话是不是暗藏深意……你们以为这个官家是朕想当的吗?!朕也想请辞,你们准不准?!”
吕好问以下,皆肃立不语,唯一一个武官王渊干脆已经跪下了。
“好了,这事情就是这样了。”就好像气忽然撒完了一般,赵官家也忽然恢复了正常,却是微微抬手相对。“按照银术可此人过往行事来看,朕觉得他十之八九要来,但愈是如此,愈不能惊惶……否则便是正中此人下怀。因为这一战,有两个关键,一个是千万不能被此人名头吓到,弃坚城而走;另一个便是千万不能以什么行在稳妥之论,匆忙召集韩世忠、王德来此,以防被围城打援!”
吕好问等人无法,面面相觑之下,只能压下心中忐忑之意,俯首称命。
而诸位相公一走,包括御史中丞张浚和御营都统制王渊也只能顾忌身份各自散去,一时只剩小林学士与刘参军了……小林学士是玉堂学士,本属近臣,而刘以兵部职方司的差遣最近留用官家身侧,成为新晋近侍,参赞御前军事,简称刘参军,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
“官家辛苦……”人一走,刘子羽便俯首感叹,但言语中不免小心了一些。
“无妨,有用便可,朕都习惯了。”赵官家无奈坐回廊下,看着满地棋子也是摇头不止。“彦修之前还有话没问出来,何妨讲来?”
“还有两问,其中一个官家却是比谁都清楚……臣刚刚正是要问完颜银术可此人过往经历与本事,以此来提醒官家。”
赵玖恍然点头,然后与一旁的冯益一起捡拾起了地上棋子。
“不过,臣确实还有最后一问。”刘子羽眼见着官家俯身捡拾,有心帮忙,却因为冯益也在,却又不好同列,只能低头捡起那片甲链,然后尴尬站在一侧,继续出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