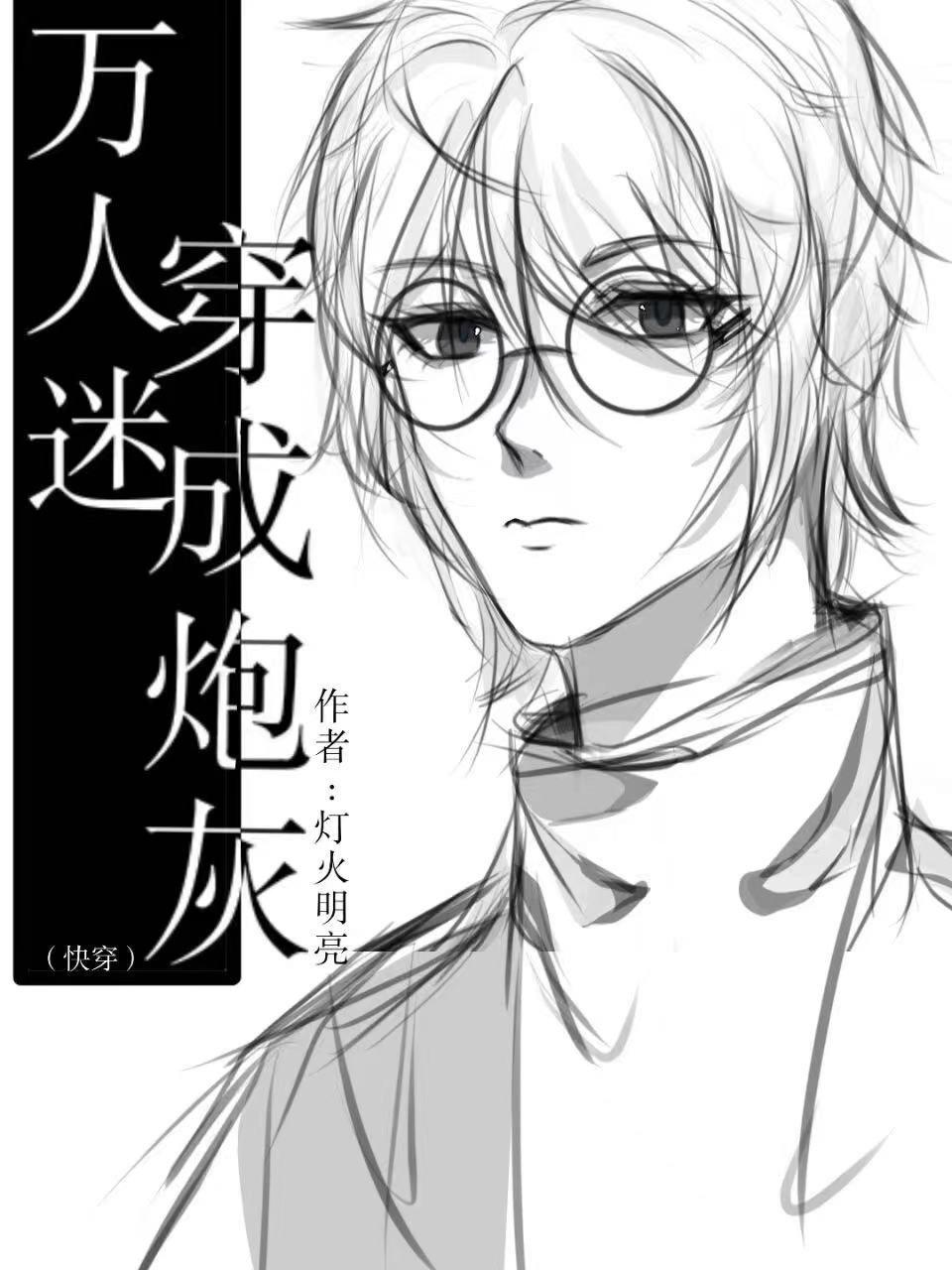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乞活西晋末免费阅读 > 第七百二十一回 蛮不讲理(第1页)
第七百二十一回 蛮不讲理(第1页)
继袭灭辽西乌桓及其周边部落之后,梅倩所部三万血旗骑军,顶着风寒,昼伏夜出,一路向北杀入幽北草原的腹地。在覆灭一个个部落并强迁一批批牧民之余,他们也顺势在幽北草原的东部构筑了一道封锁线,谨防消息过早走漏,并预防辽西草原的段氏主力前来报复。
与之同时,河北都督祖逖也带着北部防线既有的另两万骑军,秘密北出边塞,根据之前出塞商队的即时消息,或避开或控制沿途的零星部落,直插古北口防线正北三百多里的段氏鲜卑段匹所部,并在渔阳故城一战的第三天凌晨卯时,对段匹所部的核心驻地发动了骤然夜袭。
说来段氏鲜卑借着王浚的十年纵容,如今已然占据了幽北草原以及辽西草原,实力日增,嫡系部众已不下六万帐。自前单于段务勿尘死后,内部主要分为继任单于段疾陆眷,其弟段匹以及从弟段末杯三大势力。其中,左贤王段匹坐镇幽北草原,拥帐两万,若再拉上周边的附庸杂胡,轻松便能整出五万草原骑军。
只可惜,段氏鲜卑横行塞外久矣,此前也多年未与血旗军正面冲突,便是今秋的南下打草谷,他们也仅是默许附庸部落自行其是而已,所以,颇有点池鱼之殃的他们,根本不曾想到过自家会被汉人雪后突袭,更不曾召集附庸打手集结一处。由是,连个城墙都没的他们,纵是放对一战都未必能胜,在祖逖大军的突袭之下自是大败亏输,细节不予细表。
不过,祖逖不是梅倩,与段氏鲜卑并无灭家私仇,而且?段匹毕竟是段氏鲜卑的左贤王,段氏单于段疾陆眷的亲弟弟,哪怕段疾陆眷心底其实很想这个弟弟倒霉?祖逖也不愿杀掉段匹?从而令彼此矛盾激化至不可收拾。故而,他仅是俘获了段匹所部绝大多数的人员财物?而对带着两千亲军连夜突围的段匹,并未穷追猛打不死不休
“啥?这是塞外草原,咱们汉人军队怎么可以越界?还无耻夜袭你的部落?呃,草原邻居们?冒昧打搅你等好梦?解释一下,俺们这是打草谷来啦”
“啥?咱汉家富裕?不该来寻苦哈哈的牧民打草谷?呃,不然?谁会嫌弃财物更多些呢,蚊子腿再细也是肉嘛”
“啥?咱们是礼仪之邦?不该倚强凌弱搞劫掠?嘿嘿?您这就断章取义了,咱汉家同样强调礼尚往来嘛?没有光许你等草原人打草谷。我方却要守规矩讲仁义的道理嘛”
“啥?被打了草谷,这叫你等今冬咋过?卧槽?关俺毛事,多少年了,你等打草谷时也没问那些汉民该咋过吧,得了,没关系啦?都赶上牛羊,跟咱们走便是,日后纵然苦些累些,饭总能吃饱的,而且,肯定要比你等对待被掳汉民要宽仁百倍”
“啥?草原雄鹰生于斯长于斯,不想离开草原?丫丫个呸的,别好脸不要要破脸,再敢牙崩个不字,板刀面侍候,哼,真当哥大冷天跑过来,是和尔等讲道理的吗”
伴着亲切而戏谑的语言交流,以及滴血钢刀的问候,祖逖与梅倩两部血旗骑军,在敲碎辽西乌桓和段匹所部这两处幽北草原最硬的骨头之后,再无顾忌,遂兵分数路,疾驰于古北口至北五六百里的幽北草原,或猝然偷袭或直接碾压,一边覆灭大小部落,一边着手强迁,顺带再搞些以直报怨,好一番群狼狂舞。
同时,增兵足有十余万的北塞步卒,一边加强边塞防线,一边已然分兵前出,从东西中三路深入草原最远三百里,择地分别建立迁移中转站。一张针对幽北草原胡人的大网迅速成型,且高效运转。而大网之下,一批批草原牧民以及被释奴隶,则携家带口赶着牛羊,噙着转眼便被朔风吹成冰渣的热泪,乖乖的奔向叵测前程
向北绕至宇文鲜卑边境,方才折向难返辽西草原的段匹,当其带着忍饥挨冻后仅剩千余的残兵败将,可怜兮兮出现在段氏鲜卑王庭的时候,时间已然过了十日,此时的段氏单于段疾陆眷业已收到幽北草原的消息,刚刚派出两万精骑前往幽北草原阻止胆敢肆掠那里的血旗军,并正在急吼吼的征调大军,意欲再行狠狠报复一场。
怎奈杀入草原的血旗军对段氏鲜卑的反击早有准备,两万鲜卑先头部队迎头撞上了梅倩所率的骑一军团。面对人人拥有强弩的血旗军在草原上使出曼古歹战术,两万初始还气势汹汹的鲜卑精骑,很快便被折磨得不要不要,追击深入两百多里,一路浮尸两百多里,实在扛不住了,先回撤会合主力吧,结果回城又是浮尸两百余里,得,终点回到,人马却少了一半。
另一边,猫冬的草原勇士们动作委实拖沓,当段疾陆眷纠集完后续六万草原骑军之际,又是五天过去,此时的先头队伍已经用比去时更快的速度逃回了辽西草原,而血旗骑军则已带着打到的草谷,也即足有四五十万的人口、十数万金的财物兼无尽牲畜,顺利撤离幽北草原,施施然返回了北塞防线之南。
愤怒难遏的段疾陆眷如何能咽下这口气,追回被俘牧民是甭想了,他转而率军杀入辽西走廊,就近杀奔渝关防线,意欲趁着冬季河水结冰的便利,狠狠报复一场,索性夺了渝关防线。只是,刚刚在渝关下撞了两天南墙,十一月底的又一场鹅毛大雪,已然铺天盖地,面对坚如磐石的渝关冰城,他也只能灰溜溜的回家过年去也。
武的暂时不行,没少与汉人打交道的段氏鲜卑,只得先来些文的,一边遣使联络包括匈奴在内的游牧各部,一边向肇事者遣使讨要说法。由是,腊月初五,华国老朋友段文鸯出现在了祖逖所在的幽州蓟城,并受到了祖逖的热情接待。
昔年东莱一战惨败于血旗军之手,段文鸯被赎回之后,基本便失了兵权,转而负责起了与血旗一方的商贸往来,甚而成了华国在草原之上的一大代理批发商,倒也混得风生水起,潜在势力亦是不弱。不过,或因长久疏于战阵,年近三旬的他,却是少了史上的猛将气质,反因接触阿堵物太多,带上了些许文气,乃至些许市侩。
喝了两口热茶,将业已冻僵的舌头捋顺,段文鸯立马端正神色,寒声质问:“将军,贵我双方已然和平共处多年,近来也不曾有所冲突,贵方今番为何连个招呼都不打,便对我方进行无耻偷袭,难道你华国汉人就是这样秉持信义对待朋友的吗?”
“仅是打些草谷而已,贵方何必如此认真?”祖逖笑容和煦,浑不为意道,“文鸯老弟瞧瞧,此前你段氏鲜卑遣出麾下的附庸部族前来我塞内打草谷,我等不是也没去劳烦你段氏鲜卑嘛。左右仅是些鸡毛蒜皮的你来我往,过去就过去了,权当彼此活动活动筋骨,趁着入冬前练练兵嘛。”
打草谷!有将百姓一次性打完的草谷吗?练兵?有把别个所有军兵都练光的练兵吗?纵是愈加成熟市侩的段文鸯,也被祖逖的无耻言论给气歪了鼻子,恨红了眼,咬牙怒道:“这是打草谷吗?将幽北草原六百里内劫掠一空,再无几个活人,我胡人何曾如此打过草谷?再说了,今秋南下打草谷,我段氏鲜卑可未参与,你血旗军凭甚来打我段氏鲜卑的草谷?”
“呵呵,谁不知道幽北草原那些部落以你段氏鲜卑马首是瞻?千万别说你段氏鲜卑事前对此一无所知!”祖逖收起戏谑,冷声斥道,“你段氏鲜卑段匹所部既然无力约束旗下附庸部落,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取打草谷的红利,那就不配掌控幽北草原,那还留之何用?何况,谁说我血旗军打草谷,非要老老实实得按图索骥,有罪方可报复,如今可是我血旗军拳头大呢!”
“你!?你,你”段文鸯被堵得无言以对,涨红脸半天,终没压住脾气,怒声威胁道:“你血旗军如此肆意妄为,就不怕激怒所有的草原部落,从而引发大战吗?”
祖逖同样瞪起眼睛,怒声咆哮道:“大战!?幽北草原的杂碎胆敢前来我幽州打草谷,本将就敢去幽北草原将草谷给打回来!彼等倘若不服,尽管拉来帮手试试,看看我华国百万大军能否对抗。不过,到了那时,我华国就不会仅仅在幽北草原打草谷了,第一个就会去你辽西草原,顺带收回辽西郡!你且记住,犯我华国天威者,虽远必诛,且十倍讨还!”
“你!你!你等简直蛮不讲理!”段文鸯再也按捺不住,索性起身,拱手冷冷道,“将军既然毫无和解诚意,在下这就告辞,至于日后,便请将军拭目以待吧!”
“呵呵,那就不送了!本将倒是也想看看,段氏鲜卑究竟还有多少实力,那段疾陆眷是否敢来与我华国叫板!”祖逖怡然不惧,淡淡道,“还有,贵使可知会贵方单于。其一,贵方的贵人俘虏,可用昔年尔等打草谷所掳汉人折价交换;其二,幽北草原五百里之地,我方虽无兴趣移民垦殖,却将永久保持打草谷的权利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