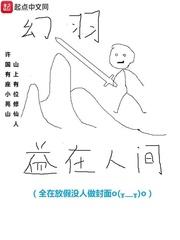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仙尊的遗愿讲了什么故事 > 第六十六章修(第3页)
第六十六章修(第3页)
哪怕到了现在,余顺提到这件事时脸上都还残留着兴奋,以及一点淡淡的疑惑,不过两种情绪都没有维持太久,便又化作了担忧。
“就是可惜,恢是恢复了,却并不稳定,受不了一点刺激,身体也完全垮了。”
说完,余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满上满是唏嘘,看向了白桁。
他在刚知道这些的时候,震惊得久久都回不过神来,忍不住就想在白桁身上找点认同,然而一转头,却发现白桁比他想象中要平静得多。
当然有知道奚陵身体具体情况后的心疼与担忧,可刨去这些,似乎又少了几分意外。
非要说的话,大概就是“竟然如此”和“原来如此”的区别。
余顺倒是也没多想,说完以后就回到了药炉前,继续给奚陵熬药,而从这天以后,白桁也不再多问,耐心地等待着奚陵慢慢恢复。
但是偶尔的,他也会有些焦急。
譬如现在,奚陵一天不好,他就一天不敢跟他摊牌。
“等你好了,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因为方才那个绵长的吻,白桁呼吸还有些粗重,和同样急促喘息着的奚陵交织在一起,让人有一种难舍难分的错觉。
但他的目光很沉静,温和专注,虽有欲望,更多的是对奚陵这个人的珍重。
奚陵被蛊惑到了,眨了眨睫毛尚且湿润的眸子,忍不住凑近,再一次吻住了白桁。
白桁一僵,手且十分诚实的,放在了奚陵的腰上。
这一次,两个人都收敛了许多。
不过饶是如此,一吻完毕,奚陵也已经完全软在了白桁怀里。
他平复了一会,突然发现,白桁的脖子有些发红。
见状,奚陵挪了挪,好奇地也亲了亲那里。
白桁一把抓住了奚陵的手腕。
“你醉得太厉害,要不我还是去给你买一碗醒酒汤吧。”白桁开口,声音莫名有些干哑。
一听到“醒酒汤”这个词,奚陵立刻不乐意了,连忙抱住了他,闷声闷气道:“不要。”
抱了一会,他迟钝的脑子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白桁方才的话,不禁有些奇怪,自己好了以后白桁能告诉自己什么秘密。
这时,奚陵又被别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。
“你的眼睛……”他摸了摸白桁的眼皮,又摸了摸自己,最后摸了摸床边的铜镜,惊讶道,“变色了。”
他明明记得,大师兄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白桁倒是十分淡定,用他那双奇特
()的暗金色眼睛看向奚陵,挑眉问:“不好看吗?”
他问得很随意,但奚陵夸得很走心,立即收回手,认认真真道:“大师兄最好看。”
白桁笑了,恨不得把奚陵按在怀里揉。
——他也确实揉了,揉完以后,又忍不住鸡贼道:“那其他师兄师姐呢?不好看吗?”
“也好看的。”奚陵摇摇头,郑重道。
只是停顿了一下过后,他又毫不犹豫地给了白桁最大的偏袒:“但是大师兄最好看。”
白桁狠狠捏了一把奚陵的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