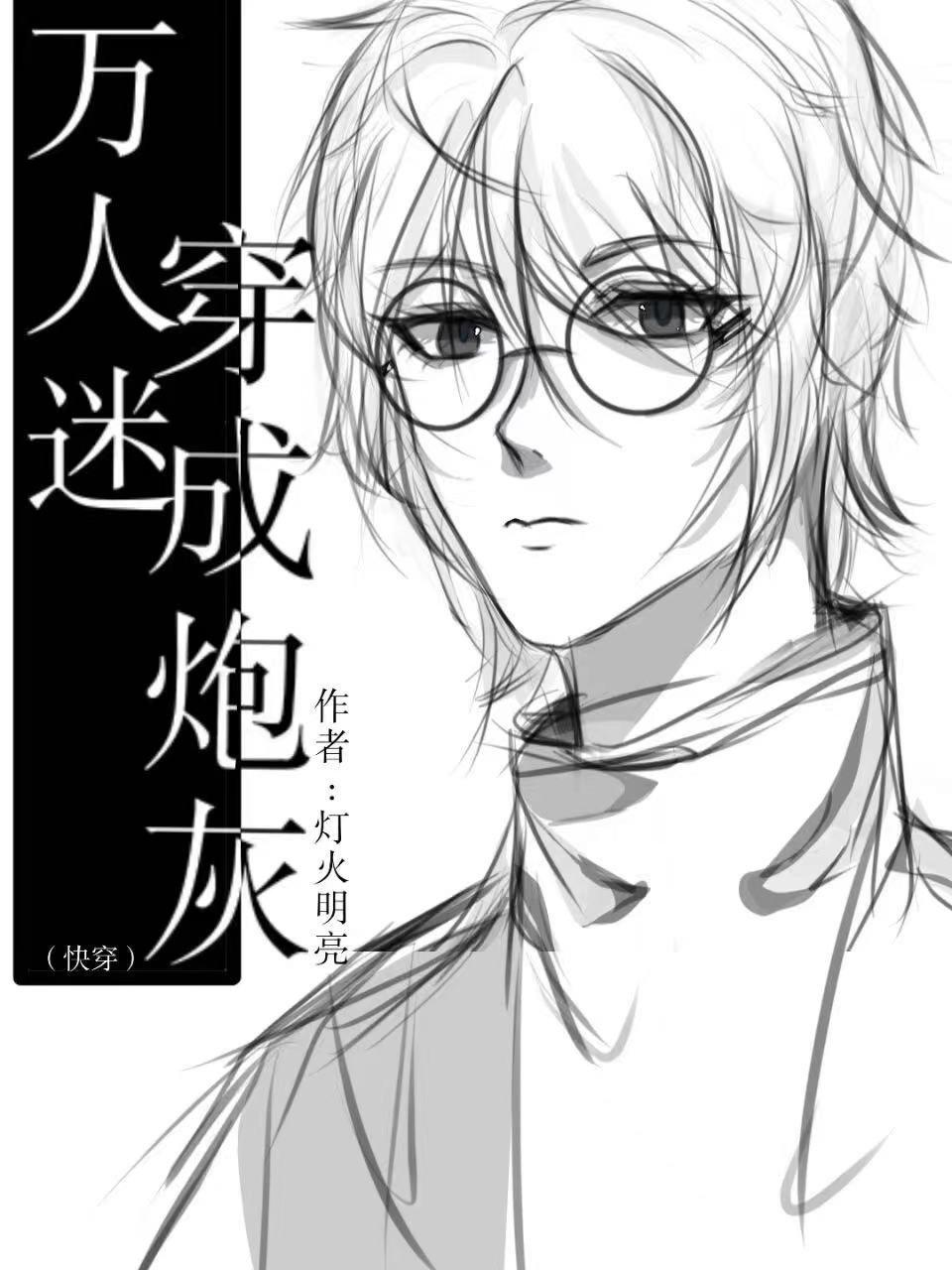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娇嫁江衔鱼 > 78 第 78 章 男女主平行番外2(第1页)
78 第 78 章 男女主平行番外2(第1页)
再次走进布庄,裴衍看向摆放在账台上大小不一的沙漏,随手拿起一个,倒转放在了窗边的花几上。
秦妧从内室走出来时,见沙漏已经开始计时,急忙凑上前,将沙漏放倒,“我还没有开始,客官稍安勿躁。”
裴衍浅勾唇角,靠在花几旁,好整以暇地看着将卷尺甩在肩上的女子,“你承诺的是两刻钟裁剪一身衣裳,难道不包括准备的时长?”
秦妧偷偷用目光比量他的身姿,试着岔开话题:“是要排除准备的时长。客官展开手臂吧。”
无意与一个小姑娘争辩芝麻大点的小事,裴衍张开手臂,任秦妧测量起尺寸。
待到量取头围和颈围时,秦妧绕到他的面前踮起脚,却还是有些吃力,“客官低一些,我够不到。”
暖融融的日光斜射入窗,映在女子的侧颜上。
裴衍倾身,目光落在女子莹白的耳朵上,被光线照射的半透,隐有细细的血管。
这样的距离着实暧昧,可量体裁衣本就是这样。
秦妧竭力忽视渐起的异样,在无人打扰的小店里,闻到了清冽的梅香。她不知那是什么名贵香料,只觉得沁心沁脾,很是好闻。
从未与男子独处过,她不适应地向后退了半步,将软尺绕过他的后颈,又轻轻一捏,量取好尺寸,随即量取了他的头围。
“可以了。”
她向侧跨去,柔声地提醒了句。自与这个陌生男子独处一室后,她的身心都在不停发颤,也不知怎就这般紧张?明明平日里也会与男子打交道,但从没有过这种窒息的感觉。
直起腰身的男子目光平静地观察着女子的一举一动,心里同样生出疑惑。为何自己会泛起浓浓的熟悉感?他可以确定,他们之前从未见过,莫不是对女子见色起意?
自己何曾这般肤浅过?
暗自摇摇头,他看向花几上的沙漏,“你还有一刻钟的时长。”
好心的一句提醒,让秦妧加快了手上的动作,当即拿起剪刀裁剪起挂在木架上的宋锦布料,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“客官是锦羽城人氏?”
裴衍从桌底勾出一把凳子,撩袍落座,“嗯。”
“怎地以前从未见过?”
“你见过很多人?”
“为了做生意,我时常与人打交道。”秦妧换了个方向站立,直面桌前的人,“客官金相玉质,若是见过,应是不会忘记的。”
适时地拍了个马屁后,秦妧睇了对方一眼,翘起唇角,略带羞怯地低下了头。
是真的羞怯了。
若非有心讨好,她可不会直白地夸赞一个陌生人。
闻言,裴衍也只是淡淡一笑,没有过多在意。从小到大,他听过的赞誉何其多,早已习惯,却没有迷失其中。
再次看向沙漏,他单手撑头,不紧不慢道:“时辰到了。”
看着停止的沙漏,秦妧放下剪刀,“小女子夸了海口,耽误了客官的工夫。作为补偿,小店想赠送客官两身宋锦夏衣,以示歉意。不知客官家住哪里,等衣裳做好,小女子会派人送过去。”
她上前几步来到桌边,抬起纤纤素手为裴衍倒了一杯凉茶,“客官消消气。”
裴衍别有深意地抬起眼,迎上女子清凌凌的目光,淡道:“你是手艺人,怎会搞错裁衣的步骤,直接起剪?说吧,留我在此,所为何事?”
能一眼看穿他人意图的男子,必然不好糊弄,秦妧自知不敌对方,索性摊开说了。
所言的难处,皆与周寂奇有关。
秦妧没指望从裴衍身上得到其他好处,只愿他做个和事佬,平息这场没必要的矛盾闹剧。
听完秦妧的话,裴衍静默片刻,玉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桌面,“所以,打从一开始,你就认出了我的身份?”
虽是问话,但裴衍语气笃定。
秦妧没有装傻,“以前在画坊有幸见过公子的画像。公子面如冠玉,令人过目难忘。”
亲耳听见赞誉的话,反倒使裴衍不知如何应答了,所幸聊起她的难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