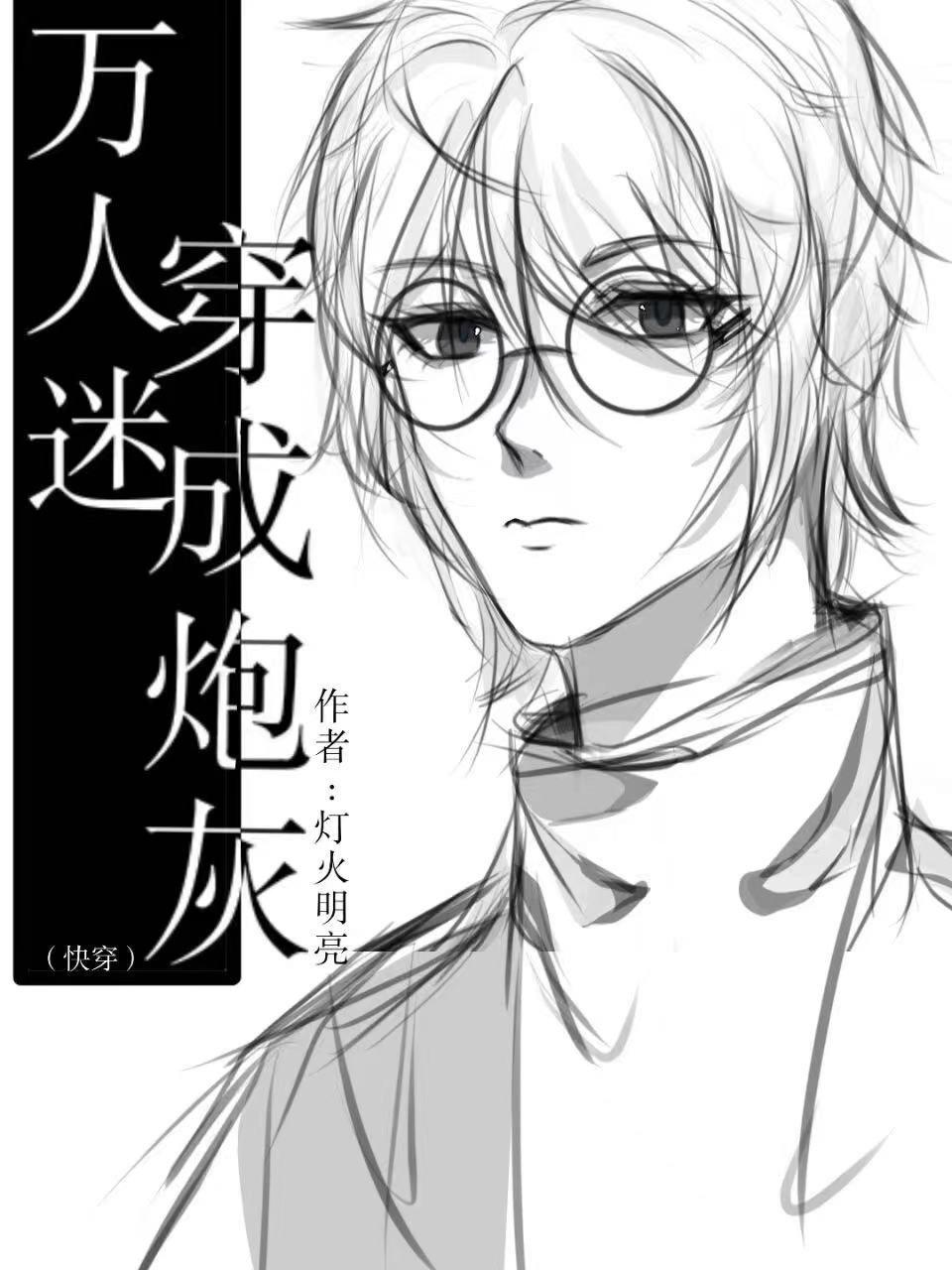3Z中文网>浪儿翻笔趣阁容溶月 > 第104章(第2页)
第104章(第2页)
雨幕遽然被斜来的长刀划破,计罗磬从上层攀舷而下,轻轻落地,截断了前往舢板的路。
“这也能跑?”他笑了笑,并不感到紧张,在这方圆十里之内找不到任何援助的境况下,这小孩儿背着水床怎么逃?
龙可羡拿袖管擦了把脸,回身拔腿就跑,爬上船舷,身子立刻跟着船身摇晃。
计罗磬缓步上前:“小女郎有点血性,这样,你若敢跳,我放你走,你若不跳,我便废了你的双腿。”
龙可羡听不清。
她垂下头,漆黑的海面犹如张巨口,咆哮着试图吞噬她。
大雨砸湿眼眶,模糊了龙可羡的视线,在这一刻,她想起的是阿勒说海上有几座小岛很漂亮,当中有道白崖。
他想在崖上盖座小院,不必雕栏玉砌,前后两进就够住了,天井要有,可以架瓜藤,可以摆水缸,最好有棵老树,树下挂个秋千,没事的时候就坐在上边数数云,夜里枕着潮声入睡,日出时金鳞从天边铺到脚下。
龙可羡看向脚下,那里黑潮翻腾,她胸口起伏,轻声说,“不怕,龙可羡一点也不怕。”
双手从湿淋淋的船舷滑开,疾风掠耳,船身在下坠时拉成了虚影,她捏住鼻子,闭上眼。
——
“哗啦!!”
——
成禄浑身透湿,发须滴着水:“我不知道,我真不知道……”
“明丰四十年,你于西南宁边城任职,明丰四十二年,宁边城遭遇海寇入侵,失守,死伤两万四千余人,你活着,”阿勒站在榻边,“明丰四十三年,西南剿匪,三战三败,你的同僚胡勤战死,你活着。明丰四十五年,你调任煜城,剿杀流寇有功,两年后平调槿州,四年后升任皮城湾督海司,总领十城海务。”
“我……我行得端坐得正,你是哪里来的贼寇……”成禄撑着口气,就要破口大骂。
“帮成大人醒醒神。”阿勒转过身。
“哗啦!”又是盆含着冰碴的水泼在身上,成禄抖似筛糠。
阿勒接着说:“两年前,你纳了房小妾,她父亲是你西南旧部,五年前出海遇到风浪失踪,你那小妾,”他抛出条金鱼,“吃穿用度皆是上乘,进府六十四抬箱笼,半数都是这金鱼。”
成禄面色发白:“仅凭金鱼,也不能说明什么……”
“老匹夫你看好了!这是西南制式!”厉天抓着成禄的头发,要他睁大眼看看。
成禄吞咽着口水:“那又如何,西南不止一个宁边城,你想凭此物就把我与计罗氏钉死?”
阿勒扯了扯嘴角。
在片刻的静默里,成禄莫名感到心惊,他看到那少年抛着金鱼,黑袖翻起,金鱼裹着强风,势如破竹地当面掷来,他倒吸口气,来不及反应,就被当头打了个懵。
被捆在椅上的身形摇晃两下,连人带椅,摔在地面,他偏头吐出口带着牙的血,嘶哑着声音说:“戕害朝廷命官,你……”
又是一道金芒疾坠。
鱼嘴撕开了手背,钻入掌心,钉进地面,成禄痛得汗流浃背。
阿勒蹲身,转动着没入他手背的金鱼:“最后问你一遍,计罗磬往哪条方向走?”
成禄张了张唇,没有说话。
“倒是条好狗,”阿勒猛地拔出金鱼,带出的血溅在他靴面上,“你家中一百二十口,连带外边养的,一百四十余口人都知道你如此忠心么?哦,听说你上个月添了个儿子,还没贺过添丁之喜呢。”
成禄咬着后槽牙:“你胆敢!”
厉天出去一趟,再进来时报道:“公子,临近船只皆无异动,只有晖县……晖县有条船踩着咱们封锁的点儿出海,至今未曾返程。”
阿勒半笑不笑地看着他。
厉天继续拱火:“成府的人都押下来了,计罗氏的十八条船都已拖至晖县,没有找着计罗磬。”
“在……”成禄垂下头,“他要我遣出战船,在晖县以南接应,走内海,绕往西南边境。”
“说清楚,”阿勒拿匕面拍着他的面颊,“哪片海域?哪条航道?”